野菰的药用和种植方式(野菰图片)
推荐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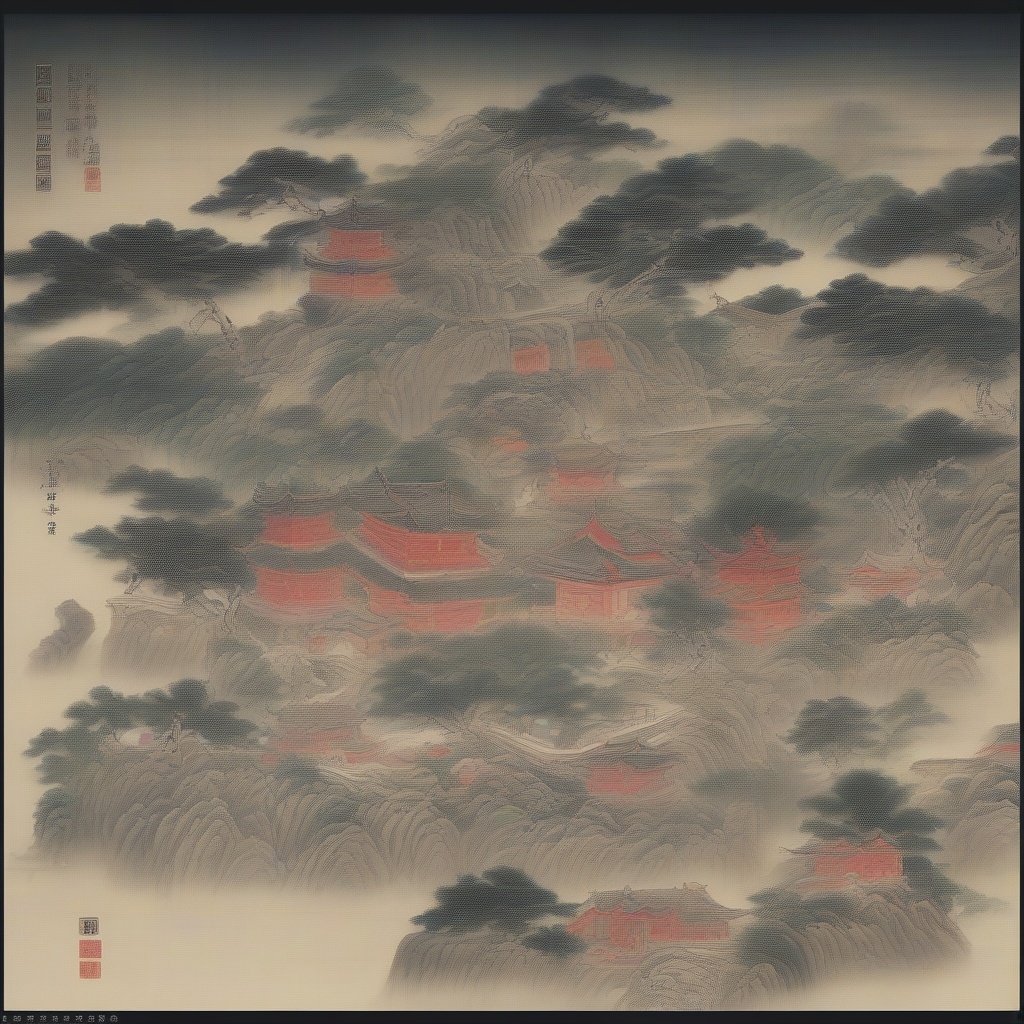
图片提供:徐太玉
野菰的药用和功效(野菰图片)
若有侵权请联系即刻删除。
走进村庄,不见一人,无鸡犬相闻,没有鸟声、风声、水声。草房瓦房楼房,所有高高低低的建筑,被荒草和藤蔓遮掩、纠缠,摇摇欲坠。
我站在院墙坍塌的家门前,一声声喊我的父亲母亲,祈盼他们打开腐朽的木门,走出来,哪怕他们苍老得像一截枯木,哪怕他们衰弱得已无法言语,只要还在。
白茆洲上的黑沙洲与天然洲
没有人应答,似千米海底的沉寂,村庄失聪了。悲伤如潮水席卷而来,我越来越急促地倒着气,抽泣。
记不清这已是第几次梦到凋敝的故乡。该说说故乡了,离开故乡三十年,我担心,也许某个清晨或黄昏,关于她的那些遥远的深深浅浅的记忆会模糊,会毫无征兆地破碎,被路过的风吹散,不留一丝痕迹。
刚说了一个梦,梦是夜的魂,那么就从四十年前的夜晚开始吧。
夏夜,竹凉床上,祖母讲完《牛郎织女》的故事,蒲扇指着银河:看,那是牛郎星,旁边两颗小星是他的儿子女儿,天河那边最亮的那颗星是织女,被天兵天将押着。
我伸手对着天空比照了一下:天河才一拃宽,这么窄,他们怎么不跨过去呢?
嗬,看着一拃宽,实际比大江(长江)还宽,宽八尺,河水滚滚翻。
我坐起来,细看,银河里一带轻薄的云雾,哪里有“滚滚翻”的模样。闭上眼睛,风掠过树梢,窸窸窣窣;再听,淙淙,哗哗,那是水流,是北冈河。
六洲暴动遗址
我的故乡白茆洲,濒临长江,乡亲们把门前这条来自雪山高原、浩浩荡荡的河流称为大江,充满敬畏。长江自西来,至此陡然北折,绕过江心的天然洲、黑沙洲、文革洲,向南——向东——向北,大弧度地圆满地环过98平方公里的白茆洲,复又东流去。白茆洲像平放的“D”,被长江深情地拥在怀中。“D”那平稳的一横,便是巍巍长江大堤,大堤这边称洲,那边叫圩。
别人说起故乡,一开口便是村头千年的古井,村后万代的青山。我们村西去一华里,有一座百年的胡家老屋,是六洲革命暴动的遗址,也是新四军七师的成立地。
此外,整个白茆洲找不到第二座上百年的房子或者一棵百年的树,唯有旭光初中原高墩子四合院内的这棵重阳树已快九十。
白茆中心校(旭光初中)内的近百岁的重阳树
白茆洲太年轻了,年轻得没有一个像样的传说,没有一句文人墨客的诗吟,年轻得失掉了一些传统的节日,或者将隆重的节日过得浮皮潦草。
十九世纪初,那些因饥荒、瘟疫、战乱、贫穷、罪罚逃离家园的人们流落到这里。辽阔的长江滩涂上,黄褐的泥土、细软的青沙,在阳光下闪着光泽;碧绿的芦苇菖蒲,迎风招摇喧哗;白鹭落满树梢,似点点星光,灰斑鸠、麦鸡、豆雁、野鸭成群结队。
这是一片丰饶的、崭新的、自由的土地。
目光湿润,脚步再也不愿挪开。他们脱下破烂的衣衫,缠起枯黄的辫子,持一把镰刀,握一柄铁锹,刈草斫枝,开沟挖渠,筑埂围田,创建家园。
江水一次次淹没田园,冲毁房屋,吞噬他们的亲人。他们一次次重来,一道圩,一道埂,一道堤坝——他们住到大江的眼皮下,与大江开门相见,互诉爱恨。
今天,我要说的是白茆洲上的一条河,北冈河。
白茆洲上沟套河塘多,筋脉一般密密匝匝纵横交错,长江自江坝分出东流的一条河——小江,在我们村后,小江又分出一条十来米宽的北冈河,向南依次流过后新地、沙垅、老河口三个村庄。右折,穿过广袤的田野,经西江闸汇入长江。
今西江闸泵站
由北向南,北冈河流经的第一个村庄叫后新地,是我的村庄。和长江大堤外的其他村庄一样,我们村建在一条高高的埂上,几百户人家坐北朝南,一字排开。我们六家住在村东,和村西隔着北冈河,依靠一座木桥相连。
北冈河的水是清澈的,清澈得发亮,在河边洗濯的人,脸上被波光映照得熠熠生辉。河水一脉脉流淌,鱼虾在油碧的水草间嬉戏,河底是洁净的细软的青沙和少量的淤泥。
沙垅是北冈河经过的第二个村庄。白茆洲形成于长江冲积滩,千百年来大浪淘沙,土质大多是松软的肥沃的油沙土,尤其是滩头江坝这一带。油沙土又叫断锹沙,一锹扎下去,是土,往下挖第二锹,便是沙,翻耕锄掘不用费多大的力气。收花生时,一把拢住茎棵,轻轻一提,一窝花生起出来,抖两下,沙土落尽,雪白的根须下坠满累累果实。
白茆洲人说:玩龙玩虎,不如玩土。就那么一锹深的土地,承载着十万人的生活,长满庄稼、树木和花草,到处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。
硕果
沙垅村的沙土比别处多,村前村后都是厚厚的青沙,沙垅人不穿雨靴,下再大的雨,雨一停,地面就干了。1979年春天我读小学一年级,学校是一个教学点,建在沙垅村西,依着北冈河,五间土墙瓦房,泥土地面,东西是一二年级教室,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,老师有时是两个,有时是三个,附近八个自然村的适龄儿童在此上学。
教室里有一条长长的木船,船底朝外,斜靠在左墙上,两头拉了粗绳索固定。同学们蹲下身,从船头或船尾狭窄的缝隙中钻进去,在立起的昏暗的船舱里睡觉、摸瞎子、过家家。有天,杨糙子(不记得他的大名了)把一只癞蛤蟆放到女老师的抽屉里,女老师抹着眼泪罢课回家,男老师怒火冲天,要扒杨糙子的皮。杨糙子躲进船舱里,任凭老师如何哄吓利诱,都不出来。老师派两个精干的男生钻进船舱实施抓捕,自己回办公室了。
农家便民小店
土墙泥地的教室里,尘土们早已按捺不住,一粒粒、一缕缕、一股股、一阵阵,跳跃,翻滚,升腾,在光柱里肆意扭动着,织成厚毡子,将我们裹在其中。瘦弱的我被人踢,被揪散了辫子,被推搡到一角,被踩踏。我奋力从自己的身体里挣扎出来,爬上一块缓缓上升的灰毡子,站在空中俯视。每个人脸上纵横的汗水、鼻涕、污渍、兴奋的瞳孔、张开的嘴巴、头发上的草屑纸片、挥动的手臂历历在目,可是,听不到任何声息,仿佛是一部默片。
冒新洲上旧房屋
在我即将飘向茫茫天际之时,老师掐我的人中,把我抱到北冈河边清洗干净。同学们沿北冈河河岸站了一溜,洗眼睛洗鼻孔洗耳朵,洗手洗脚,掬水喝,撩起水泼向别人,笑语喧哗。杨糙子洗着胳膊上的血印子,咝咝地吸气,老师顺手抠了一撮淤泥给他抹上,杨糙子欢喜地叫:不疼了不疼了。
滚滚长江东逝水
我们在北冈河里清洗、止痛、还魂。
从那时起,我知道人是有灵魂的,我没跟人说,说了人们也未必相信。而且我觉得关于灵魂的事是神圣的隐秘的,不可说,说破就不灵了,就是不敬。阴天,看着满天的乌云,一层又一层,我总觉得那是铺天盖地的灰尘,每一层上都有无数的灵魂在窥探大地。
“杨糙子事件”后,我的人生有了难言的幽微,思想开始复杂。
尘埃尚未落定,夏天到了。北冈河两端通长江,平时,河水静静地缓缓地由北向南流淌。到了汛期,流向改变,浑浊的河水南来而北下,裹挟着泥沙、枝叶和碎木片等,滚滚而汹汹。许多简易的小桥被冲毁,一些坡埂坍塌。长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不会游泳的,但汛期,没有谁敢掉以轻心,大孩子们自己拄着棍子摸水,小一些弱一些的孩子,由大人背着过河、过沟、过坝,送到学校。
水乡湿地
1979年汛期,我们村经常有孩子落水,都被救上来了。只有一个孩子死于水中——不是一个孩子,甚至不算一个真正的人,是个胎儿。胎儿的母亲跌入北冈河中,被河水冲到小江口,横在芦苇丛中。打捞尸体时,小江两岸的人都去看,远远地,只见水面上一团白花花的东西,奶奶一把捂住我的眼睛,将我拖回家。
那个溺水的四川女人,是被老光棍“小眼睛”买来做老婆的。“小眼睛”小脸小身材,一双眼睛像随意掐出来的指甲印。那个年代,娶不起、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们,委托人贩子从遥远的川贵地区买女人。
这个女子二十岁左右,个儿不高,微胖,眉目清秀,白茆洲的女人向来以皮肤白著称,这女子比白茆洲女人还白,大家惊讶于她的好看,又替她叹息。
人们问她叫什么、多大了、老家在四川哪里,她一言不发,众人便叫她“四川佬”。
“四川佬”每天都会到河边淘米洗菜搓衣刷鞋,有时拿一个碗一双筷子,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拿,只是洗洗手,将脚伸进水里摆两下,静静地站在河边看水。村里人说她太爱这条河了,推测她在四川的深山老洼里长大,哪里见过这么美丽的河。
我喜欢她,喜欢看她圆圆的粉红的脸,黑亮湿润的眼睛,大人小孩都叫她“四川佬”,唯我叫她“阿姥”,是“姑姑”的意思。她在河边洗被单,洗好了,我和她各牵一头,往外拧水,我的手劲小,被单老是脱手,每脱落一次,她就捂着嘴笑,我也笑。
让我万分惊讶和欣喜的是,她竟然识字,还会写字。她凑近我的耳朵:我念了初中呢,莫说给别人。我问她的名字,她脸色黯下来,良久,叹口气:没名字,说名字丢祖宗脸。又看向远方,目光迷迷茫茫:我是坐船来的,坐了好多的船,一条河又一条河,将来,我还是要坐船回去的。
现在,她死了,洪水冲毁北冈河上的木桥,她一个山里人,怀着孩子,竟敢涉水。广播里天天唱着歌,花儿般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,她怎么就死了?我躺在堂屋的凉床上,后门口对着小江,我看到她穿着桃红色衬衣,在后门口笑吟吟地招手:我要回家了,回四川老家了。我很高兴,想起来送送她,可是爬不起来,我烧得虚脱了。
北江西段江坝处小江
多年后,我带着孩子到长江岸边的蛟矶游玩,看到灵泽夫人祠门上的一幅对联:思亲泪落吴江冷,望帝魂归蜀道难。奠的是赴蜀地不得、投江而殁的东吴公主孙尚香。我站在春天的暖阳下,想起那位没有名字的四川“阿姥”,泪水渐渐盈眶。长江,这条滚滚河川和她的万千支流,滋养了无数的生灵,又吞没了多少生命、隔绝了多少恩爱与思念。
坚硬的山石耸立在那里,我们不怕。我们怕水,怕水的柔弱、翻滚、不可测。我们可以从荆棘丛中走出一条路,甚至,我们可以移走一座山,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运,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但是,我们的脚踏不上任何一片水面。
转眼,期末考试,考过试后的当天下午,几个同学决定去村中心小学看看。我们结伴沿北冈河向南走,走到北冈河流经的第三个村庄老河口,河上有一座陡门石桥,就是一个闸口。参观完村小红砖青瓦的校舍和操场,又到学校周边转,发现学校后面的小河是北冈河的支流时,我们欢呼雀跃,说北冈河跟着我们一起来了。
太阳落山,薄薄的暮色自四面八方盖下来,我们才依依踏上归途。在老河口的陡门桥上,背着夕阳的一边,吊着一个人,穿着黑色的棉衣,像一个倒过来的巨大的黑体的感叹号。
是薛家奶奶,生病几年了,不愿拖累儿孙,自己用一根绳索作了了结。这是后来听人们说的。
同伴们既惊骇又兴奋。有的留在现场看热闹,有的抄小路飞奔回村报告消息,作为目击者,被人们一遍遍追问。
我一个人沿着北冈河往家走,默默地思考着死亡这件事,确切地说,是思考死亡的性别和颜色。我想:太阳是男性,月亮是女性;白天是男性,夜晚是女性;生是男性,强悍有力,死亡是女性,柔弱、愁苦、无奈,村里上吊投河喝农药的,几乎都是女性。
江上
我还想:死亡是黑色的,比如那个奶奶,像一个黑色的实心球,坠入大地深处,被无边的浓密的黑色掩埋。死亡又是湿漉漉的白色,四川“阿姥”浮于江面上的那一团白,像一滴清水在宣纸上洇开,干了,没有了;又似一团白雾,被风一吹,散逸得无影踪。怪不得,逝者要穿黑衣服,子孙们戴白孝,吊唁的人套黑袖章。
原来,生命的终极不是白,就是黑。多绚丽的生命,最后都是尘归尘,土归土,都会湮灭于时光中。时光游弋于黑与白之间,是茫茫的灰。长大后,我又进一步体悟到:时光是灰尘的灰,也是灰色的灰,由灰开始,趋同黑、白两端,要么越来越浓重,隐于黑,或渐渐淡薄,吸纳于白,殊途同归,终归于无。
这些思想,当时仅是杂枝乱桠的影子,年幼的我无力理清,更无法用语言表达,今天才能以文字简要描述。
有一点倒是十分清晰,我从江面的一团白、陡门上垂直的黑中得到警示:人,不能臃肿,臃肿存在着极大的坠落危险。而且,人是有灵魂的,灵魂轻盈、自由,为了让身体和灵魂匹配,切不可太胖。
因此,我一直是个瘦子。我做了多年的瘦子,轻盈敏捷,然而近年来,却觉得灵魂重浊了,这是本来没有想到的。
从老河口归来,我开始失眠。白天我紧跟着奶奶,夜间,我会突然惊醒,小心翼翼地摸索或察看奶奶在不在床上。奶奶不在床上,我便悄无声息地起身,在深深浅浅的黑暗中寻找。奶奶也生病,我家也十分贫穷,我害怕奶奶在我熟睡的时候,像薛家奶奶一样,变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感叹号。
2019年农历五月初四,端午节前一天下午,我一个人行走于故乡的村庄、田野、河畔。原来只打算走一段,却走了一程又一程。
端午时节
村庄的房子,大多是精美的楼房,有的人家围了院墙,修了车库。门前的桃树、杏树、李子树,挂满果实,树下落了一层,鸟雀在啄食,鸡鸭们旁观。高大的栀子花树,繁星一般坠满洁白的花朵,香气也密。芦苇荡里,碧绿的芦苇在风中摇曳,修长的叶子沙沙作响。
老河口东村头,几位老人站在村村通公路边,一辆黄色的校车开过来,四五个孩童下车,爷爷奶奶们赶紧替他们背起沉重的书包,或者用简易的购物车推着。
西眺,芜湖长江二桥的引桥穿过村庄上空,桥上来往的汽车仿佛在树梢行驶。近二十年来,长江上、小江上、北冈河上,架起了各种各样的桥,坚固、美观,它们横在大地上,让天涯成为咫尺,让陌生变得熟悉,让无数的彼与此互相抵达。
芜湖公路二桥大江村段引桥
沙垅村西,当初的教学点成了空地,一片荒草杂树。四十年,记忆犹新,那段关于灰尘的时光却不在了。
北冈河,在,也不在。
昔日的河萎缩成了沟,两岸护坡上不种红豆绿豆了,水杉、大叶杨、泡桐、柳树、桑树,各种蓬蓬勃勃的树自两岸伸出手臂,互相牵挽、拉扯、拥抱、将北冈河隐蔽其中。河中,野菰瓜、野菱角、水花生、灯芯草、塑料泡沫、方便面袋、虾笼网……内容丰富,热闹非凡。行走在河边,看不到河,听不到流水声,如果不是一阵阵水锈味儿,你根本不会想到身边有一条河,一条通长江的河,你更无法想象她以前是多么宽阔、多么清亮而清凉。
拨开杂芜的蒿草,近前,暗黄的河水潜伏在浓密的草叶下,也动,不是一股,而是一丝、一滴地动,像苦苦挣扎的濒死生命,竭尽全力,透一口气,再透一口气。
江坝排灌站
我来自远方,不存到达的希望。我想起博尔赫斯的诗。这条河流的最终归宿,是回到长江还是半途枯死、闷死呢?不想探究。往往,不知所终,比知其所终要好,在懵懂的未知中,我们可以轻松达成自己的想象与祝愿。
这条河救过我,滋养了我,为我清洁面容与内心,给了我最初的思想启蒙,让我在童年时就得以窥见生命的部分真相。我想让她活着,美好地活着。
交通、住房、上学、医疗,故乡的一切都在变得更好,除了河流。一下午,我寻访小江、北冈河及北冈河那些细密的支流,有的被填平,有的干涸了,有的长满杂草漂浮着垃圾,奄奄一息。那些筋脉一样联通的河沟呢?那些眼睛一样明亮的池塘呢?
还有人。一百多年来,人们从江淮大地、皖南山区,从天南地北迁到这块水源充沛、草木丰美的辽阔土地上,现在,他们的后代正陆陆续续迁往别处,迁往远远近近的城市。白茆洲上,到处可见一幢幢空房子、一扇扇紧锁的门、一树树自开自落寂寞的花。
走过沙垅,沿北冈河向北,跨过北冈河分流出的小洼、大洼,看到我家的房子了。门前玉兰树和桂花树下,父亲坐在竹椅上拉二胡,母亲正手搭凉棚,朝北冈河这边张望,喊我的乳名。
我没有立即应答。我不能阻止挚爱的人们,在我目光之外渐渐老去,我想听母亲喊我的乳名,一声又一声。
今日摆江船
6月21日夏至,此前连降了四天大雨,弟弟拍了北冈河的视频发过来——浑黄的河水,汤汤地流淌。我心中一热:北冈河复活了,她仍是一条会逆流的河。滚滚红尘中,人生如流沙,每粒沙子都是一滴渴死的水,我们需要一条丰盈的河,一条故乡的河。
其实,白茆洲上没有冈,北冈是“摆江”的误称,百年前,这里是大江的一个渡口,人们在此登船渡江。
暑假,我驾车上长江大堤,向东行驶,到临江南折,沿外护圩顺着江水流向,向南——向东——向北,驶过“D”那优美、饱满的弧线,把白茆洲深情地拥抱。
白茆洲上跑白马,白马伏在白龙下。这片一马平川的土地上,曾泥沙狼藉,茆草苍苍;曾洪水肆虐,风雨飘摇。而今,白茆洲后有巍峨的长江大堤,前有坚固的永定圩,万亩良田中,棉花白、菜花黄、大豆玉米饱满,蔬果飘香,人们安居乐业。
回到家,洗漱毕,已是夜阑更深,人们已沉浸在各色梦境中,忧伤、焦虑、喜悦或安详。于我,父母在,村庄在,北冈河在,就是最好的世界。
轻轻拉开纱门,站到阳台上,夜风清凉。仰首,澄澈的夜空中,银河似一抹缥缈的纱,忽然想起奶奶的话:天河里的水滚滚翻。即使真的“滚滚翻”也无妨,因为有鹊桥。再渺茫的烟波上,总有一座桥供有情人相逢。
白茆套北乡村
一切起于河流,又淹没于河流。
时光如流。
时光何能逆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