荷树园电厂(荷树图片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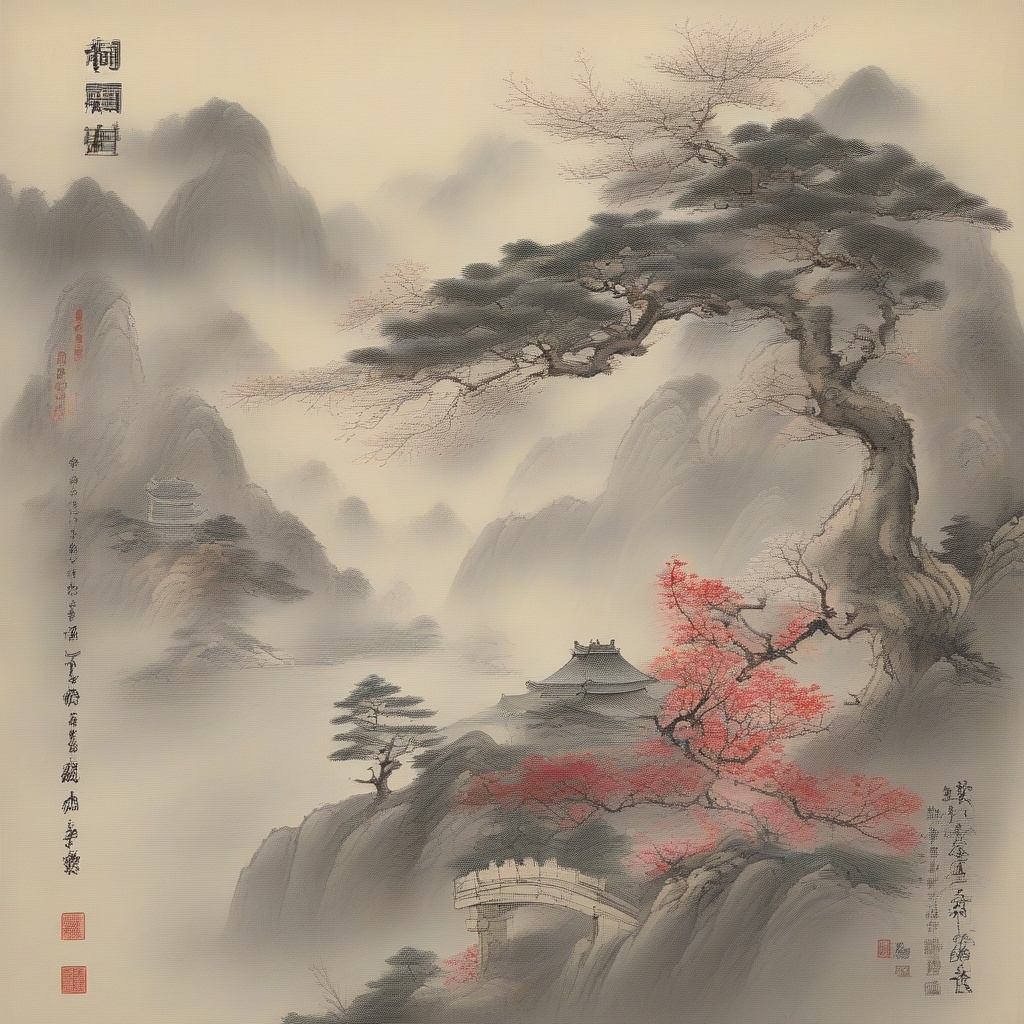
昨天已是寒露了,老家又开始摘木梓了。说起木梓,便想起了打木梓油的水碾土槽,也就是乡村传统的榨油方法,我们那儿的俗名也叫“打油”。
荷树园电厂(荷树图片)
到了农历十月初,山上采摘下来的木梓都已破壳,乌黑发亮的木仁也干透了,乡村的打油坊也开张起来。第一步把木子碾碎。以前的山村是不通电,但也难不到勤劳聪明的山民,他们一般会在村口的小河处拦一水坝,油坊就建在水坝低洼处,在油坊外面装有一个大水车,这是乡村油坊的标配,利用水坝水流的落差作动力,连结一根转轴来带动碾盘,碾盘由三个铁轮加上一个若大的圆形凹槽组成,转轴推动铁轮,铁轮在凹槽上不停打圈奔跑碾压木仁,一顿饭功夫便可把木仁碾成粉状。
第二步蒸粉,蒸粉的目的就是更好的把木仁里的油脂渗透出来。把碾好的木仁粉盛进大木甑,油坊里铁锅和木甑都是超级大号,至少可以蒸几担木仁粉,要两个大汉用竹杠抬上去,油坊的灶不高,两边砌有台阶,以便上下抬甑。灶里大火猛烧,映照烧火人的脸上红彤彤的,一脸喜色。不久甑上水雾袅袅,香气四溢,整个油坊都是木梓的味道。
第三步包枯,把蒸好的木仁粉用铁勺挖出,倒在铁箍上,铁箍下面铺有一层薄薄的稻草,油坊师傅用脚把木仁粉摊开,烫的直跺脚,稍凉,再用脚踩密实,也许有人认为这脚踩的东西吃起来不干净,可乡下人见怪不怪,那个油坊都是一样,也就是无所谓了。包枯还是要点技巧的,打油师傅前脚踩平,后脚用脚尖一钩,把铁箍周边的稻草齐刷刷的折回来,覆盖在上面的木仁粉上,宛如一只若大的月饼,掀起来木仁粉点滴不撒。
第三步撞槽,打油师傅把包好的木枯饼一装进槽树里,槽树一般选用木质坚硬且有数百年树龄的荷树或柞树,中间掏空,左边排木枯,右边的空隙塞紧木桩,那最后一个木桩只能塞个尖头,大半截还留在槽树外,油坊的檐梁悬下两根铁链,吊起一支撞杆,由油坊师傅牵头,后面再配两个精壮汉子,然后荡秋千般荡起撞杆,油坊师傅瞄准木桩,定好方向,后面两人同时发力,前后摆动起来,砰砰砰,撞杆一下一下击在露在油槽外面的木桩上,木桩越撞越紧,油槽里的油像涌泉一样哗哗往外流。我自以为,这撞槽最具有美感和力量,由于油坊里太热,打油的人都只穿着裤衩,光着膀子,露出一身犍子肉,油光闪亮。油坊师傅一边牵引撞杆头,一边喊着号子,“哎,--”后面的汉子应和着“哟喂”!如同站在山巅对山歌一般,美妙粗犷,好听极了!时常有附近放牛的孩子围在油坊看热闹,以至把牛都弄丢了!
自然撞槽是整个打油过程中最有技术含量的活,因为如果掌撞的师傅把握的方向不准,撞杆容易飞出去,甚至伤到人。如果掌撞师傅把握的力度不准,要么油榨不干净,要么把油槽榨裂,如果把油槽给撞裂了,那就麻烦大了,基本上宣告那年榨季瘫痪,为什么呢?一来做油糟的百年老树难寻,二来凿这个油槽要费多少时间和力气。所以每个油坊师傅掌撞杆时必须“快、狠、准”,撞无虚发,要力量和技巧的完美结合!如果有摄影师或画家在场,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讴歌劳动的题材!
第四步便是御糟了,经过油坊师傅他们几个的千冲万撞,终于把木枯上的油脂榨的干干净净,槽树下面的铁桶,满满的金黄透亮的木油,边沿着泛着少许白泡,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油香,劳作了大半年的山民,终于有了收获,山里人多田少,生活艰辛,来年的口粮和家里开销就指望这几桶木油了。松开槽上木桩,取出来的大圆饼状的木枯,乌黑发亮,这是拿回家去冬日烤火或下田做肥的好料!
我私下里认为:农村里最有画面感的劳作便是做豆腐,砻谷和这土槽打油了!既有劳动流汗的艰辛,又有收获果实的喜悦!如果能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申遗,那也是名至实归了。只是现在科技日新月异,机械化生产取代了这些传统手工作业,那些老物件和旧技艺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!
现在的乡村已没了水辗土槽的榨油坊,我也只能从记忆里翻出模糊的印象,以文记之,来怀念那些消失的美仑美奂的乡村技艺!
